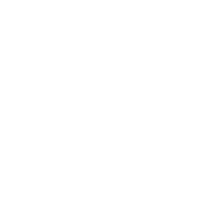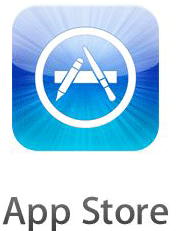第194章

- A-
- A+
“我出生身子孱弱,调理到十岁才彻底好,因不能习武,加上母亲身份低微,一直被骂是废物。”
“没办法,我只能在骑射和其他方面多下功夫。”
提到嫁人前的生活,她颇有几分怀念。
那些年虽受欺负,但不至于提心吊胆,且自由自在,能随时骑马出门。
心中惆怅上来,她随口感慨:“说来可笑,我是个姑娘家,却不会琴棋书画,甚至连女红都极差……”
这些全是顾濯缨没想到的。
“那你,现在……”
“如今,这些我都精通了。”
秦归晚顿了顿,缓缓弯下明亮的双眸,戏谑道:“成亲后,夫君手把手教我琴棋书画。”
“我为了给他绣锦衣,又苦练女红。”
只可惜,情窦初开,出生入死的四年感情,终究是错付。
她难过,但不后悔。
多无百年命,长有万般愁。人生在世,哪能事事如意?
如无意外,逃离沈家后,她此生不会再和沈晏之有任何交集。
漫长的岁月会把四年的时光磨成风轻云淡的一缕烟,最后消失不见。
谁会和一缕清烟计较呢?
“沈兄在东羌……待你……好吗?”
他明知结果,还是忍不住想问。
也许揪心的疼能提醒他,有些东西,是他不该存有妄想的。
秦归晚怔住。
那些带潮气的柴木被烤的半干,跳跃的火苗中不断窜出浓烟,熏的她眼睛发疼。
“很好。”
她低下头,挑动几下柴木,风进来,将火苗吹旺,浓烟跟着消散不少。
“我们一起流放边城时,他为了开个酒肆每天守着我,一直拼命攒钱。”
“汉人在东羌属于贱民,挣钱难于上青天。”
“哪怕同样帮别人写家书,他要少收一半的银子,别人才愿意让他写。”
“为了盘那个酒肆,他在外挣钱时每天只吃一顿饭,折腾得瘦骨棱棱。”
“甚至瞒着我去义庄帮人背尸……”
她复明那日,他拉着她去看新盘的铺子。
她盯着他看了许久,发现那双原本执笔的干净长手,满是茧子、冻疮和裂口。
俊朗的脸憔悴且粗糙。
后来,她偷偷找人打听才知道:
她眼盲在家那段时间,拓跋居为了挣钱,做尽了脏活累活。
却从始至终,没对她透露过半个字,更没让她担心丝毫。
她忽发高烧,拓跋居半夜背着她去医馆。
羌医见他们二人皆是汉人,不愿把脉开药,还放言说除非磕头求他。
拓跋居当场照办,那羌医这才不情不愿给她诊脉。
那是她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夫君弯下脊背,磕头求人。
火苗烧到边角的柴木,又起烟了。
她眼眶酸热,嗓子吞沙石似的涩疼。
实在说不下去,低下头,敛了敛情绪,再抬首,恢复了平静温和。
“他是世上待我最好的男人。”
所以她才会看在拓跋居的面子上,选择宥恕沈晏之。
不爱他,是她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丝尊严。
不恨他,是她尊重给过她赤诚之爱的拓跋居。
顾濯缨的心好像被人剖开了,冷风嘶吼着灌进去,冻住了他整个身子。
沈晏之说,流放边城时,他陪客人喝酒,她心疼地哭着照顾他。
“没办法,我只能在骑射和其他方面多下功夫。”
提到嫁人前的生活,她颇有几分怀念。
那些年虽受欺负,但不至于提心吊胆,且自由自在,能随时骑马出门。
心中惆怅上来,她随口感慨:“说来可笑,我是个姑娘家,却不会琴棋书画,甚至连女红都极差……”
这些全是顾濯缨没想到的。
“那你,现在……”
“如今,这些我都精通了。”
秦归晚顿了顿,缓缓弯下明亮的双眸,戏谑道:“成亲后,夫君手把手教我琴棋书画。”
“我为了给他绣锦衣,又苦练女红。”
只可惜,情窦初开,出生入死的四年感情,终究是错付。
她难过,但不后悔。
多无百年命,长有万般愁。人生在世,哪能事事如意?
如无意外,逃离沈家后,她此生不会再和沈晏之有任何交集。
漫长的岁月会把四年的时光磨成风轻云淡的一缕烟,最后消失不见。
谁会和一缕清烟计较呢?
“沈兄在东羌……待你……好吗?”
他明知结果,还是忍不住想问。
也许揪心的疼能提醒他,有些东西,是他不该存有妄想的。
秦归晚怔住。
那些带潮气的柴木被烤的半干,跳跃的火苗中不断窜出浓烟,熏的她眼睛发疼。
“很好。”
她低下头,挑动几下柴木,风进来,将火苗吹旺,浓烟跟着消散不少。
“我们一起流放边城时,他为了开个酒肆每天守着我,一直拼命攒钱。”
“汉人在东羌属于贱民,挣钱难于上青天。”
“哪怕同样帮别人写家书,他要少收一半的银子,别人才愿意让他写。”
“为了盘那个酒肆,他在外挣钱时每天只吃一顿饭,折腾得瘦骨棱棱。”
“甚至瞒着我去义庄帮人背尸……”
她复明那日,他拉着她去看新盘的铺子。
她盯着他看了许久,发现那双原本执笔的干净长手,满是茧子、冻疮和裂口。
俊朗的脸憔悴且粗糙。
后来,她偷偷找人打听才知道:
她眼盲在家那段时间,拓跋居为了挣钱,做尽了脏活累活。
却从始至终,没对她透露过半个字,更没让她担心丝毫。
她忽发高烧,拓跋居半夜背着她去医馆。
羌医见他们二人皆是汉人,不愿把脉开药,还放言说除非磕头求他。
拓跋居当场照办,那羌医这才不情不愿给她诊脉。
那是她唯一一次看到自己的夫君弯下脊背,磕头求人。
火苗烧到边角的柴木,又起烟了。
她眼眶酸热,嗓子吞沙石似的涩疼。
实在说不下去,低下头,敛了敛情绪,再抬首,恢复了平静温和。
“他是世上待我最好的男人。”
所以她才会看在拓跋居的面子上,选择宥恕沈晏之。
不爱他,是她给自己留下的最后一丝尊严。
不恨他,是她尊重给过她赤诚之爱的拓跋居。
顾濯缨的心好像被人剖开了,冷风嘶吼着灌进去,冻住了他整个身子。
沈晏之说,流放边城时,他陪客人喝酒,她心疼地哭着照顾他。
 我要评论
我要评论